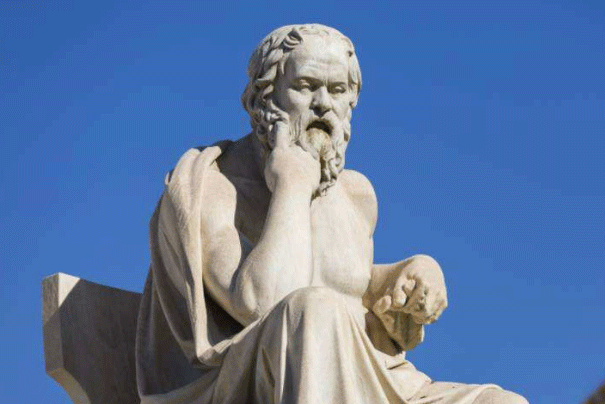吴怡:吴怡博士在《易经》上的态度和看法
本文为吴怡教授在第八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上的主题演讲节选,我们转载自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公众号,是想与大家分享一下,吴怡博士在《易经》上的态度和看法。在吴怡博士的观点中,《易经》应该先是一本哲学著作,其次才是占卜所用。而且前面还有个胡适遇见荣格谈论《易经》的小故事……
胡适初遇荣格的故事
拜读申荷永博士寄给我的《荣格与易经》一书的初稿,我非常高兴,因为好几次我和他踫面时,都劝他把荣格有关易经方面的研究和故事一一搜罗下来。在我的朋友中,只有他有此能力,而我对荣格那么多的著作,自觉无能为力。所以希望用他的研究,取巧的略知一二,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在这里我先把荣格对《易经》了解的问题放在一边。该书中写到荣格遇见胡适的故事却引起我特别的兴趣。
这是在1936年9月16至18日,哈佛大学三百年校庆,荣格与胡适同获荣誉博士而作专题演讲。事后两人碰面时,荣格问胡适有关《易经》一书,胡适直截的说:“噢!那本书不算什么,只是一本有年头的巫术魔法选集,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两人话不投机,交谈似乎很不愉快,此事令荣格梗梗于怀。
直到二十年后,写给朋友鲁道夫·凯勒(Adolf )的信中他还提起:“比如中国,像胡适这样的哲学家羞于知道《易经》。道的深远意义已经丢失,取而代之是人们对火车和飞机的崇拜。”可见荣格心中的遗憾。
丨吴怡博士在做演讲
这次碰面,胡适已是四十五岁,在中国推行新文化运动大有名声,所以荣格非常看重他,称他为哲学家,满以为胡适对《易经》有卓越的研究,却不料,胡适的不屑态度,使荣格被浇一盆冷水。
心中也许自忖,受他如此推崇的《易经》,难道在中国学者眼中,是这样的不堪吗?他自然难释于怀。至于胡适,当时年少得志,意气风发,看到荣格对《易经》的醉心,也许是以为西方学者的幼稚,才会这样没有耐心的用“巫术魔法”四字判死《易经》,毫无解释的余地。
胡适自称有历史考证的嗜好,难道他对《史记》的文王演易,孔子晚而喜易,一无所知?或故意视而不见呢!总之,他们两人不幸没有共感,就像今天男女关系的不来电。所以两人同样的失落,错过了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大好机遇。这个故事对于今天的我,看起来,更是扼腕叹息不已。
这次的失落,对胡适来说,失去了传扬中国文化的机会,其实在当时胡适等人根本轻视中国文化,因此这也是自得其果。但对荣格来说,却是一大损失。
因为此后荣格只能靠卫礼贤的《易经》译注去了解和运用《易经》,他只能限于蓍草或铜钱占卜的神秘方法,只能看到占卜中每一爻,或每一卦的卫礼贤翻译的意思,未能进一步看清《易经》全书,以及《易经》和老庄,和整个中国文化的关系。而最大的不幸是荣格终其一生,并未来到中国访问。

丨荣格(左)胡适(右)
关于易经,这是我想传达的态度
我因他两人的故事引起了很大的冲击,才写下了这篇文字。在这里,我不是想要告诉荣格什么,而是借此说明今天我们研究《易经》,或介绍《易经》给西方人士时应该有的态度。
《史记》中只说文王的“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一句话,前人都无深论。如果只是把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这并不稀奇,因为那是自然之数,绝不可能得到六十五卦,也不会是六十三卦。
问题是如何把这六十四卦排成次序,这虽然也很费工夫,如后人说的错卦和综卦,但如只限于符号,而没有意义和文字,这也仅是符号的安排而已。重要的是每个卦起了一个有意义的卦名, 而安排的次序就必须根据挂名有理路可循,这不仅是大学问,而且是有一套思维的哲学系统,所以我认为文王在狱中的演六十四卦,至少有了卦名,也有了思维推演的智慧。
文王出狱后,有很长的时间治理国家,据说他在位五十年,活到八十余岁,因此他能把治国的经验、理想和哲学放在六十四卦的三百八十四爻中,就成了全部的《易经》。
至于卦辞和爻辞在后代的传授中,文字上有所修饰或改易,这也是古书流传的普遍现象,不足为奇。
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易经》在文王手中,还是一部哲学性的著作,只是他由于自己的感性,以及避免商纣的残害,而用了很多象征性的语言来婉转表达他的思想。
到后来,至东周之初,因为要适应君王们不能读原著,只求一字一句的问卜,才被筮者变成了占卜之书,自此之后,《易经》的哲学性被人忽视了,占卜反而变成主体。
老子和孔子都承继了《易经》的思想
《易经》用于占卜,在左传和国语中都有实例。
该书藏于王府,本为君王所用,而解卦的都为史筮之官。老子是周代守藏史,正是史官,所以他对于《易经》,不仅是守藏者,并且是运用者,当然是知之甚深,而影响他的思想也是极自然的。
老子一书提到圣人有二十六次之多,且以圣人之治为理想。这个圣人,传统都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圣王,而老子生于周代,也许指周代始祖文王更为贴切。文王虽一心要推翻商纣,但知时机未成熟,所以尽量表现出谦卑柔弱、无为不争的低姿态,如谦、小畜、蹇等卦,这正是老子一书讲柔弱、无为的中心思想。
至于孔子访周遇老子,老子当然会介绍《易经》一书给他,那时孔子在四十六岁到五十岁之间,所以后来他读易时就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这里,孔子明言“大过”,可见他心中有“大过”这回事。
他说如果五十学易,再加数年,正值他五十四岁做司冦的时候,他上任七天便斩少正卯,此事子贡便不赞成,到孔子晚年读易时,遇到“恒”卦,才发现以前讲德治,而斩少正卯却是法治,做得太快,变得太激,不能执德以“恒”,才有被人排斥,愤而离鲁之行,这是他心中之悔(详见拙著孔子的悔与《易经》)。可见《易经》在孔子心中的地位了。至于他的写《十翼》,明见于《史记》,更是他思想的最大成就。

面纱往往美丽耀眼而吸引人。占卜对《易经》的传世也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要不是它,《易经》不会如此受人喜爱,传得那么久易经起源的新说,那么远。
在我的易经课中,虽然我只讲义理,但也让学生们知道一点古人如何占卜的方法,学生们知道了占卜之法后,就一心只想问占卜之事,而根本忘了义理。占卜虽神奇,但毕竟是术数和方法,不是背后的那套整体思维和智能。
就拿左傅襄公九年,穆姜问卜的史实来说。穆姜是鲁宣公之妻,淫于臣子叔孙侨如,后来两人合谋想推翻成公,反而被成公放逐到东宫。她自知生命垂危,问了一卦,原卦为艮,变卦为随,因艮的五爻皆变,只有第二爻不变,所以她问题的答案在随卦的第二爻,爻辞是“系小子,失丈夫”,是指淫于小人,而背叛丈夫,这不正是穆姜的写照吗?真够神奇。
而解卦的史官,为了讨好穆姜,说随的意思是出,劝穆姜可以出走。那料穆姜虽行为不检,也深通易理,她指出随的卦辞是“元亨利贞,无咎”,应解为能“元亨利贞”才可以无咎。而她对“元亨利贞”四字完全违背,所以不能无咎。结果她还是死于东宫。
据这一史实,可见占卜虽神奇,但仍以义理为原则。《易经》爻辞上的吉凶,只是占卜的文字,但我们在义理上的作法,仍然可以改变爻辞,转凶而为吉。
卫礼贤的《易经》英译本有其局限性
所谓“局限性”是指卫礼贤本为基督教传教士,他信仰的是上帝。由于上帝和《易经》中的天道的不同,再加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背景的相异,所以他的译注和《易经》的原文,及其思路自然有很多差别,甚至有显然的错译,这也是任何译本所不可避免的。我们无意责备贤者,但却必须了解它的局限性。
譬如他把《易经》中的“命”字译为命运(fate),如讼卦九四的“复即命”,及鼎卦象辞的”正位凝命”等。这是卫礼贤的未能完全了解《易经》作者文王的“天命”思想。
另外他的译注自言是本于清朝李光地的《周易折中》(以宋明儒家解释为主)和宋朝程伊川的《易传》(译注的简介中还弄错了以为是程明道)。全书中,受这两本书的影响随处可见。
宋明儒家虽然直追孔子,但究竟不如孔子的开放,至于对老子更视为异端。所以卫礼贤译注不能跳脱宋明儒家的解释。
譬如,荣格为了替卫礼贤译注作序时,占了一个鼎卦,问题答案在九二爻“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伊川和朱子都把这个“仇”放在初爻上,颇为勉强,卫礼贤用了《周易折中》里该爻的案语,把疾当作嫉妒,其实《易经》其他处的疾,都作毛病解(《易经》用了八次疾字,在豫、复、无妄、遯、明夷、损、丰,和兑中,七次都作毛病解,一次作快速解),而不作嫉妒解。卫礼贤却把疾译为嫉妒,荣格不知中文《易经》,也就随该译文,当作朋友的嫉妒。
其实就鼎卦各爻来看,“仇”应指九三和九四,这两爻挡住了九二和六五相应之路,而九三的“耳革”和九四的”折足”正是它们的病。“耳革”是骄傲,不听忠言易经起源的新说,“折足”是太过刚强,不能行进,因九四阳刚,直逼六五,两者都是骄傲自是之病。
荣格占得此爻,如果解为戒骄傲自是,能够自省,重视修养,就远比不在乎别人不嫉妒为佳。如果荣格能从这方面了解,我想他应该更喜欢《易经》的了。至于在道家方面,《易经》本为儒道两家的同源,但卫礼贤在道家方面却很少发挥。
所谓”非局限性”是指卫礼贤的精神抱负。尽管卫礼贤的译注有许多错译,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易经》精神的感应或荣格的共时性。
最近我看到他孙女为他所作的影带,全部描写他翻译《易经》的专注和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卫礼贤是传教士,但他对《易经》的投入可说超过我们一般研究《易经》的学者,他是用他的生命去热爱《易经》的,他的坟墓上便是用八卦图形来陪伴他长眠。这点使我深深的感动。
本来我写这一节的标题是“基督教的上帝和《易经》的天道没有感应。卫礼贤对天命没有感应。”现在我却加以修正,认为卫礼贤的译注中虽然把“命”解为命运,而对《易经》和儒家的天命没有感应,但他的热爱《易经》,宣扬《易经》,也是他的一种天命。
他是传教士,他的传教本为了上帝的意志,即上帝交给他的天命,但他对《易经》的宣扬,似乎是对《易经》的一种天命感,在他的译注中,也仅几处用到上帝两字,可见他是直接从《易经》而证入的,但他对宣扬《易经》的天命,也可以和他宗教的上帝的天命相通。我所谓“非局限性”,就是指在文字《易经》之外,他那种热爱《易经》的精神,是他整个生命的投注,是超乎文字的,是无限开放的。
对卫礼贤来说,他的译注本身是有局限性的,而他对《易经》热爱的精神却是非局限性的,我们不因他的译注的局限性中有许多错译而妨碍了他精神的非局限性。我们也可用他的非局限性的精神去转化他的有局限性的译注。同样,我们也不可只拘执于有局限性的文字语言而当作非局限性的精神本体。
譬如《易经》的文字,以及《易经》流传的各种解释,都是有局限性的,而作易者(文王,或孔子所指圣人)观天地气象和人事的变化,写在三百八十四爻中的这种智慧乃是非局限性的。我们研究《易经》不能只在文字的有局限性中去求解,而要能冲破局限性,超脱上去,体会那非局限性的天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易经》全书在既济卦之后还要讲一个未济卦了。